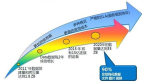敌军阵亡统计:美国防部长麦克马拉1965年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。
「大数据」时刻准备着改造社会,从看病,到教娃,甚至可以教会汽车自己上路。数据正成为新的经济推动力,和重要的生产资料。企业,政府,谁都能通过数据,给看着不得劲的东西来个优化。
但,凡事总有两面性。「大数据」蚕食个人隐私。特别是,老子不就淘宝上搜了一下志玲姐嘛,连网易都给我推荐各种仿真玩具。这让一个老问题显得更加严重:看数据,拍脑袋的决策,往往错误百出。没有比罗伯特·麦克马拉的故事更适合说明这一点的了。
麦克马拉是个数据狂。他在1960年代越战战事趋紧时,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长。他热衷于收集任何他能得到的一切数据。通过严谨的统计学分析,他坚信可以从纷繁的复杂局势中,得到正确的决策。世界在他的眼里就是一锅混沌的数据汤,但通过描述,归类,筛选,定量,最终能被人的意志所驯服。麦克马拉寻找着真相,而真相就藏在数据中。他所收集的数据,其中就包括了「敌军阵亡数字统计」(wiki)。
麦克马拉在哈佛商学院念书的时候就培养了对数字的迷恋,而且他在24岁就成为了助教。二战中,他在五角大楼挑选的精英团队里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,在一个叫做「统计控制」小组,他们分析从战场获得的数据,进而为世界上***的官僚机构提供决策建议。在此之前,军队如若眼盲。比如,军队不知道机场的数量,发布,位置的情况。数据分析帮了大忙,从而使弹药补给更有效率,在1943年就帮助节省了3.6亿美元军费开支。现代战争需要物资的合理高效分配,而麦克马拉所在的团队成就斐然。
战后,这个团队的成员,继续在美国经济领域施展才华。当时福特汽车正深陷危机之中,陷入绝境的亨利·福特二世把烂摊子交给他们。就和他们虽然不懂打仗,但也能帮了盟军大忙一样,他们对造车同样一窍不通。但,他们仍然如魔法神童一般,硬是把福特汽车从倒闭边缘救了回来。
麦克马拉很快地位飞升,开始插手福特生产的各个方面。强迫工厂经理按照他的计划生产,无论他的计划是对是错。当他命令所有库存的同一型号的汽车零件,必须在新型号开始生产之前用完,愤怒的生产线经理干脆把老的零件就近扔到河里。工厂里开玩笑说,被扔在河里的50年代的老车,多到都可以让人列队过河了。#p#

麦克马拉在福特执政期间,曾强势给福特汽车标配安全带,但市场反响一般让福特又回到了动力至上的老路。
麦克马拉就是把理性和对数据的依赖置于直觉判断之上的典型,他会用他的定量技巧去改造任何工业部门。1960年,他被任命为福特汽车主席,但这个位置干了没几周,他就被肯尼迪点将,成为美国防部长。

1960年,当麦克马拉(肯尼迪身后)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时候,他自谦:我完全不胜任。
越南战事逐步升级,美军火烧屁股的时候,这场战争很明显已经成为一场「面子战争」,而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利益。美国的策略就是想逼迫越南土共回到谈判桌上来。然而,衡量达到这个目的的进展,就是看敌军阵亡数。越共阵亡数字每天都见报。对于鹰派来说,数字就是进展;对于反对派,这就是这场非正义战争的证据。阵亡数字成了定义那个时代的标志。

芝加哥街头的反战游行
麦克马拉依赖和迷恋这些。他梳着***的大包头,系着一丝不苟的领带,觉得自己瞪着报表就能对千里之外的战况了如指掌,好像靠这些计算和图列,就能让他得到堪比上帝般的,接近事实的标准方差。
1977年,也就是越战结束后两年。前驻西贡大使,Douglas Kinnard将军,出版了一本意义重大的报告,叫做《战争经理人》,披露了数据量化决策的陷阱。仅有2%的美国将领认为「敌军阵亡统计」能代表战争进展。「纯属扯淡!」书中写道,「就是公然撒谎,部队故意夸张数字,目的就是取悦那位无比热衷于数字的麦克马拉。」
美军在越战中对于数据的错误迷信,误判,和对于信息的局限性的教训,对即将到来的大数据时代是个很好的前车之鉴。我们手里的数据可能是很不可靠的,数据可能带有主观偏见,可能被错误的分析和使用。更糟糕的是,数据可能没呈现它本该呈现的。
我们比想象地更容易被弊大于利的「数据执政」所统治。这种恐惧来自于,我们被无意识地被绑架在数据分析上,就算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分析根本就是错的。想知道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情况?用标准化测验来衡量老师的表现,然后处罚老师和学校就行了。想预防恐怖主义袭击?简单,搞一张监视名单和禁止入境名单来管住领空就行了。想减肥,没问题,下载一个App算一下消耗的卡路里,连健身房都不用去。#p#
就算在大数据执政里,一些行家里手也常掉入陷阱。Google的一切都是基于数据。基于数据的战略使他们走向今天的成功。但也时不时地给Google下套。两位创始人,Larry Page和Sergey Brin,长期坚持对应聘者提供高考成绩和毕业平均成绩。他们认为,高考成绩代表了一个人的发展潜力,而毕业成绩代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。就算40多岁的老江湖也被要求提供相关成绩,这让他们彻底懵了。Google坚持这样做,直到内部调查显示,学校成绩和工作业绩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为止。
Google应该多长个心眼。数据没有留给个人在一生中做出改变的空间。数据把数据的增长当做智慧的拓展。但数据根本无法体现人性的复杂,衡量一个人的能力要比科学工程计算难得多。Google的两位创始人也是从采取强调独立性,而不是成绩的蒙台梭利教育方法(wiki)的学校出来的才子,用基于数据招聘的方法显得很奇怪,因为照这样的标准,从比尔·盖茨到扎克伯格,就算是乔布斯也不可能被录用,因为他们拿不出像样的成绩单。
Google嗑数据已经走火入魔。前Google高管Marissa Mayer来到Yahoo后,竟然要求员工测试41种不同的蓝色,以决定哪种蓝色是人们最常用的,并用在自己的网站的工具栏上。2009年,Google的***设计师 Douglas Bowman 愤然辞职,因为他没法给所有事情定下明确的标准。
Douglas对Google的工程师文化忍无可忍
他说:「我最近的争执,是关于一个边框应该是3,4,还是5个像素宽,然后非要我证明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我真的没法干了。」他写了篇博客宣布了他的辞职决定,「当一家公司被工程师执掌的时候,浓郁的工程师文化决定了问题的解决方式,就是把所有问题都拆分成一个个琐碎的简单逻辑。所有事情都需要有数据支持,***搞残了公司。」
这就是数据执政。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美国在越战的困境,「敌军阵亡统计」的片面性,和不是基于更严肃全面的评估,对越战的失败负有部分责任。1967年,当国内的反战浪潮高起,麦克马拉承认道:「事实就是,关于人的复杂处境,是无法用图表,小数点和负债表所能完全表现出来的。但,真相是可以通过缜密分析获得的。如果不去分析可以分析的对象,就是只满足于得到不完整的洞见。」如果正确的数据用在正确的地方,不相信数据就是有病了。
麦克马拉后来在1970年代掌管世界银行,在1980年代,他成一个鸽派,不但声讨核武器,而且是环境保护的支持者。晚年又出版了一本回忆录,在回忆中,他深刻检讨了自己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的战争思想和决策,他说:「我们错了,大错特错。」他逝世于2009年,享年93岁。但他对包括数据质疑,特别是「敌军阵亡统计」上,他坚持己见。他承认,一些数据统计可能出错,但他认为,如果事物可以被统计,那就应该被统计上来,阵亡数字只是其中之一。
大数据可以成为改善药物生产,学习方式,个人行为的基础。但它具有的意料之外的力量,会让我们犯和麦克马拉一样的错误。使我们变成数据的奴隶,痴迷于数据的推论,而忽视了数据的误导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