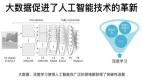为了抵御网络所带来的碎片化信息冲击,有的人特地将周日设置为“断网日”,在那天他完全不上网。这个行为有点像一个犯了毒瘾的人,定期去戒毒所戒毒,治不治本不知道,但至少能稍微治一下标,或者说,让自己体验了一番另外一种生活。
也许是因为觉得一天的“断网日”仍不足,有的人尝试过连续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不上网,还有的是甚至是一两个月不上网。而 The Verge 的 Paul Miller(保罗·米勒)比较彻底地体验了“断网”的滋味。
一年前,他宣布自己将断网一年,彻底隐居,不论私底下,还是工作,他都不使用网络。至于电脑、iPhone、iPad 等数码设备,统统设置成“断网”。为了避免自己偷偷上网,他甚至逛电子市场,买旧式的诺基亚手机。
至于他这么做的理由,其实和许多希望断网的人一样,他认为互联网不应该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:
——我如此“熟悉”互联网,以至于我的生活全部都是它,这让我十分担心。我非常确信,互联网已经入侵了它不该去的地方。
这个行为有一种行为主义、实验主义的味道,我们很想知道,经过一年的断网,保罗·米勒到底有何感受、感慨。断网是否真的让人的生活,社交等各个方面变得更好了。但保罗·米勒在文章里写的第一句是,“我错了。”断网固然带来了美好,但没有网络也挺糟糕。
一开始他觉得没有网络的生活十分的“自由”,与真人线下碰头,投掷飞盘,骑单车,以及研究希腊文学。他还写了半本小说,而且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写一篇随笔,发布到 The Verge 上。头几个月,他的老板因为他的写作数量减少而表达过一次失落的情绪,这是之前没有过的,以后也没有。
这一年里,保罗·米勒的体重减轻了 15 磅(6.8 公斤),所有人见到他都觉得他看上去非常棒。他的注意力也得到了增强,以前阅读 10 页的《奥德赛》都觉得困难,而现在,只要坐着他就能轻轻松松阅读 100 页。如果那本书简明易懂,或者激发了他的兴趣,那么几百页也很正常。离开互联网,他发现产生想法的途径也不太一样了。
保罗·米勒的姐姐感到十分高兴,因为以前他总是一边对着电脑,一边听她说话,让人沮丧,而离开了网络之后,他就不再这样。她觉得自己的弟弟更加关心她了。
如今有了 Google Maps,我们去哪儿都想不起来要用纸质地图。而离开了网络之后,保罗·米勒发现使用纸质地图并不困难,至少他在纽约市里没有迷过路。由于不用电子邮件,他开始用邮筒来收发信件,这种感觉比较奇妙——他一周会收到十几封信件,而不是以前,一天几百封电子邮件。
但他也发现了“断网”本身的虚妄之处,他说:
——在虚拟的世界中,也有许多“真实”的东西;而在真实的世界中,也有许多“虚拟”的玩意。
断网并没有真正让人一个人变得富于创造性,无聊以及缺乏刺激,反而让他养成了新的陋习,变得习惯于被动消费,而且有社交退缩的迹象。过去一年,他骑单车的次数没有多少,他的飞盘上满是灰尘。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家中的躺椅,他常常躺在上面玩游戏,或者听有声读物。
除此之外,没有了网络,与别人的联系变得困难。保罗·米勒发现,发短信总比打电话容易,而发起 SnapChat 或 FaceTime 也比到别人家里作客容易。平常他在家,电话都没有一个。父母总是担心他是否仍然健在,于是常常让他姐姐过来探望。而如果在网络上,这一切都容易得多。
此外,因为没有网络,保罗·米勒和自己关系最铁的哥们失去了联系——其中一个去了中国之后,就再没电话往来,而没有网络的帮助,他又不能取得联系;另外一个住在纽约,背负着沉重的工作压力,平时没有太多时间聊天,关系也变得疏远了。
保罗·米勒说,当初离开互联网,觉得自己将变得更加“真实”。但经过了一年时间,他发现,真实的自己以及真实的世界已经与互联网紧密相连,无法挣脱。
——我读过为数不少的博客、杂志文章,书籍,它们与网络如何令我们孤独、愚蠢,或者又孤独又愚蠢相关,因此我开始相信它们的说法。我要找到到底互联网“对我们做了什么”,这样我才能反击。但,互联网并非个人的追求,它实际上令我们彼此相连。